赵园:与一些有非凡气象的人物相遇让我心存感激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中与研究生同学(右三为赵园 张中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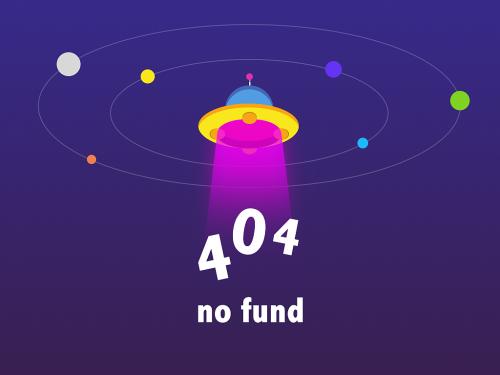
◎答题者:赵园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7月
简历
赵园,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想象与叙述》《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红之羽》《世事苍茫》等。
1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
以年龄论,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不能再好了。2013年退休,事后看来,真的是一种解脱。首先是由单位的人事环境中解脱,几十年间在社科院文学所,有太多无谓的消耗。此外,退休使我摆脱了“课题”之为“任务”,可以选择自己想做、认为应当做的题目。尽管工作的强度没有降低,心态已然不同。这对我很重要。
庆幸于退休,也因为有些事不能再拖。时间很严酷。去年秋天以来,我就发现自己的思维能力在钝化。这不能不让我紧张。最近看俄罗斯世界杯,一再提到的,就有时间。一代球星的离去,你纵然不舍,不忍,也无可奈何,是不是?你自己被时间消磨,虽不能与那些巨星相比,“自然规律”的无情,对谁都一样。
2如果把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划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您会怎么样来划分?现在的学术环境和您那个年代相比,您认为有什么变化?
似乎没有出于设计的阶段划分。一定要划,只能将研究现当代文学与考察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分为两截。这样分也有道理,因为后一段工作更遵循学术规范。我有机会还会谈到,在我看来,参与推动引入学术史的视野与学术规范,是陈平原的一大贡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学术转型,人们往往归结为外部环境,我却认为,即使没有外部的变动,中国的学术也会转型。不只是为了与国外学术对话,更为了学术自身的发展。
转向明清之际,我个人最大的收获,也在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因了向经典学习而有的对学术的敬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荒芜已久,给你一种错觉,似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清之际不然,这块土地有许多真正的大师耕耘过,你不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对于初涉学术领域者,这是一个适时的警醒。我从来不“狂”,却见过别人年少轻狂。或许要有更多的阅历,更广泛的比较,才能将“狂”转化为创造力。
我还想说,我退休得正是时候。虽然少了在职研究人员由课题制获利的机会,能够不受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限制,在长达几十年间,几乎所有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对于我,太幸运了。若不是贪恋这种条件,我或许会选择离开,也确实有机会离开。我进入文学所,在“文革”结束不久。汲取了“文革”前搞“集体项目”的教训,我所在的研究室鼓励个人研究。我不敢说这种条件对所有的同事都有益,我确实看到一些年轻同事的荒废,但我自己受益是无疑的,没有这种条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转向明清之际。
3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之前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您更偏爱哪个?
我著述不多。一定要我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之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挑出一本较少遗憾的作品,那只能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吧。较之之后关于明清之际的写作,那一本写得比较生涩,但其中生机流溢。写那本书,处于思想极其活跃的状态,感触之多,自己都无暇应接。有过学术工作经验的同行或许都能体会,这种状态,你一生中或许只有一次,不大能重复。在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中,那确实是仅有一次的经历。
做现代文学研究,也偶有这种状态,比如1985年写萧红。那也像是一种遇合,以你当时的状态恰恰遭遇了理想的对象。
两段学术工作一定要问我更偏爱哪个,只能是后一段的吧。两个领域对于我都是陌生的。无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无不是“空着双手”。但后一段毕竟更有挑战性,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难度方面。进入这一历史世界,与一些有非凡气象的人物相遇,让我心存感激。这在我,也是学术工作中的最好补偿。
4不管是引人关注的学术著作《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还是随笔集《独语》《红之羽》等,您对自己的著述最看重的是?
这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学术性的与非学术性的。我会写一点随笔,现在也还在写。随手记下偶尔想到的一些,飘忽不定的思绪,往日生活的片段,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思考,等等。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手边随时有纸和笔,行囊中也一定有纸和笔。我会告诫年轻学人,让写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不会那样惧怕写作了。
如果要我自己比较,我更看重的仍然是自己的学术作品。并不只是因为正业、副业,而是投入更多,“用情”也更深。这两种文体各有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学术工作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并非随笔所能——当然,真正的大家除外。
5假若倒退十年,您有哪些遗憾最想弥补?
如果你问的是学术,我想,没有特别想弥补的遗憾。因为做每一个题目都全力以赴,至于做得好坏,是水平问题。
如果不限于学术,那么我应当承认,学术这个行当,对从业者的要求太苛刻。回头看,你会发现牺牲了太多。比如长期的功利性阅读,失去了为读书而读书、为了享受读书而读书的乐趣。那种单纯的快乐只存在于记忆中。此外还不得不压缩其他爱好。每一种职业都有代价。我并不后悔当年选择了学术。我没有足够的活力,创造力。做学术,禀赋优异自然好,若没有天赋,仍然可以以勤补拙。但如果有年轻人向我咨询,我或许不会鼓励他们选择学术。他们可以有更丰富多彩的人生,活得更加生机勃勃。
6您希望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曾有年轻人向我提问:从事学术研究是一种“纸上的生活”,你对这种生活“有没有产生过虚无感?”“有没有想象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那种实践型的、参与型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位年轻人显然已有成见在先,认定我是排斥“实践”“参与”的书斋动物;而且有等级划分,“实践型的、参与型的知识分子生活”优于“纸上的生活”。提问者或许以他的某些师友为尺度,以为不合于那种尺度的选择都不大可取,至少需要解释。
我真的不认为需要解释什么,需要为自己不符合某种期待而抱歉。这种划一标准、成见在前的质疑,只是让我觉得无奈而已。我与现实的关系,在我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意识中,也会以随笔的形式直接表达。我不认为从事学术与关心现实不能兼容。你如果选择了学术作为职业(且不说“志业”),就应当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学术工作者,做好你的专业研究。至于用何种方式对现实发言,可以有多种选择,也可以选择不选择。不选择,不存在道德或道义问题。明清之际时论苛刻,却也仍然有通达的见识。对这种见识我特别欣赏。“以理杀人”是传统文化中最不应当“继承”的东西。读一读《儒林外史》,就知道那种道学面孔的可憎。
我从来不以“公知”自期,我尊敬那些能对公共事务作出有力反应的知识人。也有号称“公知”却以辩护不公不义为己任者,所谓人各有志。至于我自己,如果有一天讨论当代史,一定会凭借了已有的学术训练,使自己的言述坚实、有说服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还是要感谢学术经历对于我的赐予。
7您认为做学问之道是什么?
这是个太大的问题。我不长于大判断。我关于学术的思考,写在了学术作品的后记中。《想象与叙述》附录的两篇《论学杂谈》,不全是为年轻人说法,更是我个人的经验谈。能不能与年轻学人分享,我没有把握。他们有他们所处的情境、治学条件。也像我们不能复制前辈学者的学术经历那样,他们也没有必要复制我所属的一代的“治学道路”。
我看重的,更是年轻人对职业的态度。职业伦理与其他伦理实践相关。一个人没有职业的责任感,我很难相信他在其他事情上能够负责。
8您认为当下作为年轻人应该如何培养阅读古典经籍和理论著作的兴趣?
我曾劝一个年轻同事读点古籍。我确实觉得,知识基础薄弱,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突出。因为缺少了某些知识准备,我们甚至不能参与与专业相关的议题的讨论。例如关于新文化运动。去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无论官方还是学界都悄无声息,安静得有点奇怪。明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想必会大举纪念。但你仍然绕不过有些问题,比如如何重估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如何在眼下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回望五四。
中国现代文学史前后仅三十年,这样重大的问题都不能面对,作为专业人士是否合格?我自己因为后来转向了明清之际,与原来的专业拉开了距离。但在有些场合,还是会以现代文学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发声。比如关于启用《三字经》《弟子规》之类作为蒙学教材,比如对于传统中国的宗族文化缺少应有的批判。《家人父子》的《余论》两篇,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写“家人父子”这一题目,问题意识就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
至于理论,我承认自己缺乏相关的能力,却始终有理论兴趣。“文革”前读大学本科,就自觉地读马恩两卷集,“文革”中则读官方推荐的马列的六本书。1980年代新思潮滚滚而来,虽然吃力,仍然努力地跟读。直到近年来读不动了,还尽可能由别人的论述中间接地汲取。我希望年轻学人有理论兴趣,有对于新的思想观念的敏感,有对于其他学科最新发展的关注。你可以在其他方面“偏胜”,但既扬长又补短有何不好?
9您研究写作之余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有哪些满意的“玩儿票”经历?
我的兴趣还算广泛,对电影,对音乐。甚至会每四年世界杯当一回“伪球迷”。最近看纪录片《梦巴萨》,很陶醉。感兴趣的不只是小罗(罗纳尔迪尼奥)、梅西的球技,还有巴萨与加泰罗尼亚民族认同,一个足球俱乐部与一个国家的历史。1980年代曾经写过几篇影评——充其量不过是“观后感”罢了。对于影视文化的兴趣却始终不减。欣赏的不只是剧情,有时候更是演技。但爱好归爱好。记得读到过池莉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当然说的是我辈凡人。民国学人,就大有一辈子做了多种事且无不成就斐然的。
发现自己仍然保持了知识方面的饥渴,对于陌生领域的好奇心,包括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文化,网络用语,等等,汲取知识仍然如恐不及,我很欣慰。如果有一天成了“九斤老太”,那就真的无可救药地老了。
人们关于“学者”尤其女学者往往有刻板的印象。记得有一回聊天,谈到当时巴西女足的玛塔,男同事竟然惊呼起来,像是撞见了怪物。这似乎也是一种病,模式化,类型化,先入为主。生活世界那么广阔,学术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我,是占据了最多时间的一部分,也仍然不是全部。
10假如能和一位古人对话,你最想和谁、对他(她)说什么?
我不大想象这种事。也不以为自己能和任何一位古人对话。我只需要读他们,想象他们就够了。读史景迁写张岱的那本,反而不想见到张岱了。国外汉学家的想象力太丰富。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绘声绘色”。我自己绝不会尝试写历史故事。倒不是有考据癖,而是总会想到别种可能,或许,如若。我不相信自己真的能贴近那个时代,走近那些人物。但我说过,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幸运的事。
不想象与古人对话,或许也因了年纪。我曾经对鲁迅极其倾倒。读研期间接触郁达夫,也一度迷恋。那更像是一种迟来的青春热情。我没有小说才能,不能在几十年后把那种情感体验清晰地描述出来。进入明清之际,也曾经为人物吸引,比如对方以智,比如对当时的北方大儒孙奇逢。只是这时候的我,心理已经不再年轻,倒是容易看出表面光鲜背后的瑕疵,叙述得似乎周严中的破绽,也就不那么容易过分投入。这样一来,学术工作难免少了一点乐趣。
11您怎么看待退休之后的“闲”,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自己的养生之道?
我已经说过,退休后我的写作强度不减,还没有过真正的退休生活。我希望把手头的工作大致完成,让自己进入退休状态,读点闲书,听听音乐,随意走走,逛逛超市,买块衣料做件衣服。或许最想读的仍然不是“闲书”。比如已经在搜集书单,如果当时视力允许,想集中一段时间读关于苏东的书。
我不大注意养生。过得随性,物欲不那么强烈,大概就是我的养生之道。
12您同时代的同学朋友,有很多著名人士,您平时怎么交往?您最看重朋友的品质是怎样的?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师”“大家”“学术重镇”“著名人士”太多了吗?至少我不“著名”。我倒是以为,无论我还是我的那些友人,学术成就、学术贡献都被高估了。有一句老话,“头重脚轻根底浅”。缺少“根柢”,腹笥太俭,是这一代学人的普遍状况。我们凭借的,固然是各自的努力,却更是机缘。“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这一机缘。现代文学不像古代文学,积累深厚,也就有了较大的空间可供施展。我只能说,我和友人各自尽了自己的努力,在学术上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这就够了。至于生前身后的名,别人的褒贬毁誉,真的用不着过于介意。
近些年老友间情谊仍在,交往却渐疏,也是发生在时间中变化。我得到的较多的,是来自比我年轻的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人生在世,需要的并不多。那种可以信赖、必要时可以托付的感觉,真的很美好。
对于人,我最看重的,是我已经提到的“光明俊伟”。这更是境界、气象,而非你所说的品质。或许应当承认,我还不曾在生活中遇到过称得上“光明俊伟”的人物,我自己更不是。
13您认为幸福是什么?
这也不是我长于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或许因了早年读童话、民间故事的经历,我常常会想象另一种生活,宁静的,单纯的。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在一个内部关系正常的机构,做一份不需要过分占有你的工作,也无需随时为时政揪心——那应当是一个更正常的社会。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可以这样生活,我会觉得幸福的吧。
这不像是什么高大上的回答。我们这一代曾经有共同的箴言,比如青年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不知当下的年轻人是否还能像我们当年那样被这样的箴言打动?
参考资料:http://www.ztwang.com/news/11305.html